-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 (2009年8月1日)
- 外文书名: The Compelling Image
- 丛书名: 高剧翰作品系列
- 平装: 301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16
- ISBN: 9787108030214, 7108030217
- 条形码: 9787108030214
- 商品尺寸: 24.4 x 17 x 2 cm
- 商品重量: 581 g
- 品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etails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气势撼人》所收录即当时讲演的内容。此处,我仅仅稍事改写,并附加几处简短的说明。这些讲稿(在此已重新编次为篇章的形式)的原意,并非在于交代整个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史;有关十七世纪画史,我在别处另有处理,拙著中国画史系列中,第三册与第四册将分别以晚明与清初的画史为探讨主题。
媒体推荐
高居翰的《气势撼人》,是目前为止有关十七世纪中国绘画的论著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本。
——方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高居翰基本上倚赖两个工具:一为其对绘画风格的精辟形式分析,另一则为其以画家之身份背景及生活方式为探讨作品内涵之切人角色。前者来自于他在西方美术史方面的训练,非一般中国传统学人所熟习,后者则出于他长年以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钻研,以及一种具有审慎批判态度的理解。通过这两个利器在画家作品上的联系,他遂得以引导读者进入时代的文化深处。
——石守谦(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美术由于传统太长,无论是资料掌握或观念的自由度,都形成入门的障碍。高居翰的中国美术史,提供了一个新颖而不同的视野,对我们重新面对自己的传统有耳目一新的启发性。
——蒋勋(台湾东海大学美术史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高居翰(James Cahill) 译者:李佩桦 等
目录
三联简体版新序
致中文读者
英文原版序
地图
第一章 张宏与具象山水之极限
第二章 董其昌与对传统之认可
第三章 吴彬、西洋影响及北宋山水的复兴
第四章 陈洪绶:人像写照与其他
第五章 弘仁与龚贤:大自然的变形
第六章 王原祁与石涛:法之极致与无法
简写书目对照表
注释
图版目录
索引
序言
1979年3至4月间,我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CharlesEliot,NortonLectures)之邀,发表了一系列讲演,本书所收录即当时讲演的内容。此处,我仅仅稍事改写,并附加几处简短的说明。这些讲稿(在此已重新编次为篇章的形式)的原意,并非在于交代整个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史;有关十七世纪画史,我在别处另有处理,拙著中国画史系列中,第三册与第四册将分别以晚明与清初的画史为探讨主题。如果读者对于突然切入此一主题感到无所适从,可以参考上述画史系列的首二册,即《隔江山色》与《江岸送别》,以建立背景知识,不过,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实则并不需要此种背景知识,因为本书写作的原意即在于作为专书发行。
从任何相关的参考书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绘画研究的范畴多集中在十四世纪左右的元代,以及十七世纪的明末清初阶段,其他的阶段几乎完全被忽略。这两个阶段乃是中国画史中极关键的时刻,一旦我们了解了其中的堂奥之后,同样地,也能进一步地明白分列在这两个阶段之前或之后的绘画景况。本书所处理的乃是明末清初这一阶段,亦即十七世纪的中国绘画,而且,藉由当时代绘画与相关的画论著作,我们也进一步地探讨了一些艺术史性与艺术理论方面的课题。
诺顿讲座以诗为依归,而“诗”所指的,乃是一种较广义的意思,也就是说:凡是借文艺形式来传达意义的,都可算是“诗”;这也正是我在书中所要处理的主题: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中究竟有哪些含义呢?而这些作品是如何传达这些含义的?我运用了一些新的方式来探讨书中这些作品,希望能够尽力看出这些画作在含义上,是否有某些结构存在呢?有些重要的课题,诸如画家的社会处境等等,我仅轻描淡写地点到为止。至于明末清初的历史是否透露出了当时绘画的形态,这并非我所关心的主题,我所在意的,反而是:明末清初的绘画充满了变化、活力与复杂性。从这些作品之中,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当时代的社会处境以及思想上的纠葛呢?或者,当时耶稣会引进西方观念,而满清入主中国,凡此种种,我们是否能够从这些绘画中,看出中国人在面对这些重大的文化逆流时,是如何调整自我的轨迹的呢?
在我原本的计划里,此次讲座的推演正如中国宇宙论中的开元创世一般。在进入主体之时,如一片“混沌”,我们用清楚明确的阴阳二元观点来切人中国绘画,这约莫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一种艺术理论了:一端是在绘画中追寻自然化的倾向。
文摘
插图:

第一章 张宏与具象山水之极限
十七世纪的中国绘画为什么这样吸引我们?无疑地,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画家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作品。但是,这一时期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仅仅在于个人作品的美感与震撼力。诚如罗樾(MaxLoehr)所曾经指出,中国早期绘画系一长期、缓慢而持续不断的发展,到了宋代,在大师们极致的成就中,达到了高峰,其后,元代画家放弃了在绘画中刻意追求气势雄浑的效果,而为中国绘画史开启了第二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此一发展在明末、清初时,达到最高点。宋元以及明清之际,乃至于其后的几十年间——亦即十四与十七世纪——是中国晚期绘画史上关键且具划时代意义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不但产生了许许多多不朽的巨作,同时也开创了许多绘画的新方向。在这两个时期里,从事各种复古创作的画家们对于整个绘画艺术的过去,进行了影响至深的再思考。在这两个时期里,传统自省,进而反馈,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这种过程自来便是中国文化中所特有。再者,到了晚明和清初,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画家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更较以往来得迫切,而且受到画家更为慎重的处理。这些问题到清初以后,便几乎不再受画家们所关切了。
中国到晚明阶段,已经享受了超过两个世纪的太平岁月,多数画家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显得安定繁荣,画家和艺术赞助人均能过着颇为稳定自足的生活。明代于1644至1645年间正式结束,在大臣们自相倾轧残杀之际,中国沦入了满清“异族”的统治。但明王朝统治的崩溃,实际上自十六世纪末即已开始。朝廷内激烈的党争、君主的昏庸无能,以及宦官的嚣张跋扈,在在都使得仕宦一途既无道德成就感,也无利可图。当守正不阿的节操无法为有德之士赢得应有的报偿,当正直之士可能因坚持原则而遭杀身之祸时,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再也难以为继,甚而整个儒家行为与思想体系都受到了质疑。儒家体系的崩溃过去虽也屡见不鲜,但却不曾如此次般地导致人们对整个体系的全面而广泛的质疑。李贽与狂禅派人士信奉个人主义式哲学,他们所着重的,乃是自我的实现而非社会的和谐,这与鼓吹回归儒家根本和政治改革的运动,同时并存着。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和艺术都走极端的时代。这种情况固然让有强烈自我目标的艺术家获得解放,但却使得那些需要稳固的传统,以及遵循规范的艺术家们相形见绌。这种情况表现在艺术上,则是绘画风格史无前例地分裂,同时,也迸发了持续百年的旺盛创造力。
如果我们尝试在这里描述十七世纪绘画的多样性,恐怕也会导致类似且令人不悦的支离破碎感。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依循常法,试图在这个时期的绘画或甚至在整部中国画史当中,找寻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创作目的与方法上的单一特性。一般而言,近五十年来,中国绘画的研究多半(而且理当如此地)着重于画史延续性的建立,以及验证各发展阶段里此种延续特质之显现。有些对整个传统的看法,很早以前就已提出,之后便一再地被复述至今,诸如:中国绘画重表现山水之真谛,而非稍纵即逝的现象;其目的在重视内在的本质,而非外在的形式;其根本上是一种线条与笔法的艺术;特重临摹过去的作品,尤其到了画史晚期更是如此;而且原创力也绝少受到强调,等等。这其中的每种说法都含有部分真理,然其真实的程度如何呢?我们可以用一种相对的说法来说明。有些中国或仰慕中国文化的作家对欧洲绘画也持雷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欧洲绘画反映了西方文明中物质主义的特性,过度地沉迷于人像,且泰半未能开发敏感笔法里所含的表现力。可怪的是,有的人会因为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而恼怒,但是,他们自己却往往很能接受上述那些有关中国绘画的泛泛之谈,而且,他们对于那些想要开导我们,为我们讲述中国绘画之“道”及其玄妙本质的作家,也都表现得心悦诚服。
在经过四个世纪逐渐了解之后的今天,我们(按:指西方)视中国文化为单一整体的习惯,仍旧挥之不去。此一观念的背后,无外乎认为中国人总在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并采行中庸之道。,虽则此一观念在其他学科的中国研究中,早已丧失其权威性,然在中国艺术的领域里,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且被普遍认定的观点。(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有敏锐眼力的艺评家们,可以在看完一个十七世纪独创主义画家的作品展之后,却认为眼前的作品似乎与较为人所熟知的宋画并无不同。他们会问:所谓个人独创主义与非正宗派,究竟是什么呢?另外,我也听过有人对欧洲绘画作类似的反应。一位眼力深厚的中国艺术家暨评论家,曾在浏览完美术馆所展出的涵盖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至毕加索等西方画家的作品之后,抱怨这些画作的风格雷同,并惋惜画家忽略了正确的笔法。所幸,今日已少有人尝试在那样的层次上去议论中国绘画。由于其他领域的艺术和文学相关理论,以及中国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辩证方法论上绝佳的例证,我们终于被追觉知到了中国绘画史的变迁与消长,并开始从每一时代、每一画派,或甚至每一位画家本身所面对的多重选择,以及从各种流风对立的理路出发,来建构画史。而我研究十七世纪绘画的方法,即是属于这一种。
首先,我们可以用两张晚明阶段的绘画来阐明一种熟见的二极性【图1.1与图1.2】,一张是那种依传统形式所建构而成的作品。另一张则至少尝试相当忠实地描绘一段自然的景色。(若有读者发现难以立即看出哪一张画代表哪一种画法,其咎正在于我适才所描述的现象:想在视觉上区别作品的异同,必须先在视觉上对于素材本身有某种熟悉度。不过,这两张画应该要不了多久,便可看出其明显的不同。)这两张画,其中一张是董其昌l617年的作品,根据画家自己的题识,他所画的是位于浙江北部吴兴附近的青弁山。另一张则是同时代,较董其昌年轻的张宏的晚年之作。画上的年款为l650年,所以应该算是清初,而非晚明的作品。虽然这两张画的创作相去三十余年,却不影响我们进行比较,因为我们同样也可以拿画家相隔仅数月的作品来作相同的比较。张宏画里所描绘的是距南京东南约五十英里左右的句曲山。
借这件作品,及其所在的创作背景,我们恰可引出晚明画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与选择。张宏活动于苏州(参阅地图),且就我们所知,是号职业画家。董其昌则系邻近以松江为中心的山水画派宗师,同时也是一显赫的文人士大夫,对他而言,作画乃是一种业余的嗜好。在这段时期里,含董其昌在内的中国绘画理论家,以“行家”和{‘利家”来区分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对董其昌者流而言,这种分野虽则实际上颇为含
糊,然在理论层面上,却有其根本的必要性。董其昌所属的松江派业余画家经常指责同时代苏州画家商业化的倾向,并攻击他们对过去画风一无所知。张宏的作品确实没有任何明显或刻意指涉古人画风的意图;另一方面,董其昌画上的题识则告诉我们,其格局乃承袭自十世纪某大师的风格,不过,实际上他所采用的却是另一位十四世纪大师的形式结构。对同时代具有涵养的观画者而言,这两个层面所指涉的古代风格,他们必定能够一目了然。我们可以将这两张画视为自然主义与人为秩序两种相反且对立方向的具体表现,此种相反与对立亦即是贡布里希(ErnstGombrich)在论及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时,所提出之古典的对立:“可以想见,一幅画若愈是……忠实于反映自然的面貌,则其自动呈现秩序与对称的法则便愈形减少。反之,若一造型愈有秩序感,则其再现自然的可能性也就愈低。”(董其昌作品中所呈现的秩序感,以及内在于此秩序感的反平衡和特意造成的无秩序感等,详见第二章 讨论。)
董其昌与其青弁山的画题之间,因而便隔着一层密实的古人画风的帘幕。董其昌曾在别处提及,有一次他行船途经青弁山,忆起了曾经见过赵孟与王蒙两位元代画家描写这座山的作品;在董其昌心中,当他在认知此山的真实形象时,这两幅画的记忆必定已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赵孟烦的画已经佚传,不过,王蒙的作品却仍流传至今,是董其昌用来标示其画作里文化轨迹的另一艺术史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董其昌画作的主要元素,并非记忆或实地写真,而是作品本身与过去画史之间复杂的关联性。画家对于笔墨结构的关注,完全凌驾于空间、氛围和比例的考虑之上,而笔墨结构则部分源自于既往的作品。同时,纯水墨的素材表现也对作品的抽象特质有所助益:相对地,张宏所描绘的句曲山,是以淡彩烘染,展现出画家对空间、氛围与山水比例细微的观察。晚明的评论家唐志契在《苏松品格同异》一文中,简要而贴切地道出了此二派画风的区别,亦即“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适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准绳也。笔之所在,如风神秀逸,韵致清婉,此士大夫气味也”。
董其昌本人在揭示有关真山真水与山水画之区别的名言中,也同样地暗示云:“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换言之,若你要的是优美景色,向大自然里去寻;若你要的是画,找我即可。
这两张画的不同,非仅在于风格、流派或手法上殊途同归的问题,而在于两张画分属不同类型。我们习于将中国山水画视为单一类型,实则它是多种类型的组合,这在晚期的山水画尤其如此。董其昌《青弁图》属于“仿古”创作,他在题识中也如此写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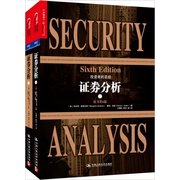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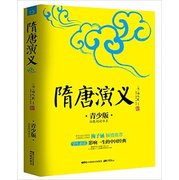
 Facebook
Facebook Twitter
Twitter Pinterest
Pinterest Google +
Google +